
文/董小玉、何艷
在當(dāng)代藝術(shù)展覽中游走的觀眾,常常會(huì)陷入一種認(rèn)知困境:面對(duì)那些既不“悅目”也不“和諧”的作品,是否還能用“美”來評(píng)價(jià)?英國(guó)普利茅斯大學(xué)藝術(shù)史系教授伊麗莎白·普雷特約翰的《美的,藝術(shù)的》,恰好從深遠(yuǎn)的角度回應(yīng)了這一話題。這部著作不僅梳理了美的概念史,更構(gòu)建了一場(chǎng)跨越千年的美學(xué)對(duì)話,邀請(qǐng)讀者重新思考這個(gè)看似簡(jiǎn)單卻無比復(fù)雜的問題——藝術(shù)是否需要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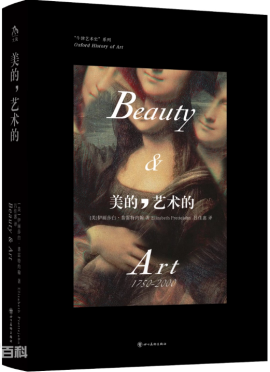
美的譜系學(xué):從客觀法則到主體覺醒
伊麗莎白·普雷特約翰帶著獨(dú)特的學(xué)術(shù)洞察力去解構(gòu)美的歷史。她敏銳地指出,柏拉圖的“理式美”與亞里士多德的“有機(jī)統(tǒng)一”理論,共同構(gòu)建了西方美學(xué)最初的二元框架——前者將美視為超越性的永恒真理,后者則關(guān)注藝術(shù)作品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這兩種充滿張力的美學(xué)法則在中世紀(jì)演變?yōu)樯袷ッ琅c自然美的辯證對(duì)立,直到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才在阿爾貝蒂的《論繪畫》中獲得創(chuàng)造性結(jié)合。
除了對(duì)最初客觀法則的揭示,伊麗莎白·普雷特約翰在對(duì)助推個(gè)人主體性發(fā)展的啟蒙美學(xué)闡釋上,也超越了傳統(tǒng)的康德解讀。她將康德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與同時(shí)代英國(guó)經(jīng)驗(yàn)主義美學(xué)家埃德蒙·伯克的“崇高論”并置,揭示出18世紀(jì)美學(xué)革命的雙重軌跡:一方面是對(duì)審美判斷的哲學(xué)純化,另一方面是對(duì)美學(xué)體驗(yàn)的心理探索。這種并置使我們看到,浪漫主義畫家如弗里德里希的作品《霧海漫游者》中,不僅有個(gè)體意識(shí)的覺醒,更有對(duì)伯克式“愉悅的恐懼”的視覺轉(zhuǎn)化。
至此,伊麗莎白·普雷特約翰施展她淵博的知識(shí)體系與清晰的行文思路,讓我們得以由遠(yuǎn)及近地層層探尋“美”之發(fā)展的歷史譜系,以及了解不同時(shí)期美學(xué)發(fā)展的側(cè)重點(diǎn)與超越性;并且在創(chuàng)作主體與呈現(xiàn)客體的辯證結(jié)合中,學(xué)會(huì)從主客觀的不同視角去發(fā)掘作品中美的可能性。
現(xiàn)代性的悖論:在解構(gòu)中重建美學(xué)價(jià)值
伊麗莎白·普雷特約翰打破了“現(xiàn)代主義等于反美學(xué)”的簡(jiǎn)單敘事。她指出,即使是最激進(jìn)的達(dá)達(dá)主義,其反美學(xué)姿態(tài)仍是對(duì)美的另一種關(guān)注方式——通過否定來確認(rèn)。杜尚的《泉》并非簡(jiǎn)單地否定美,而是將美的判定權(quán)從藝術(shù)家轉(zhuǎn)移到觀眾與藝術(shù)體制,這實(shí)際上拓展了美的可能性領(lǐng)域。
作者對(duì)格林伯格形式主義理論的批判尤為犀利。她揭示出現(xiàn)代主義“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口號(hào)背后所隱藏的美學(xué)教條:將“創(chuàng)新性”本身神圣化為另一種美的標(biāo)準(zhǔn)。這種洞察解釋了為何波洛克的滴畫雖然拋棄傳統(tǒng)美感,卻發(fā)展出關(guān)于“過程之美”的新范式。現(xiàn)代藝術(shù)對(duì)美的解構(gòu),本質(zhì)上是一場(chǎng)美學(xué)的創(chuàng)造性破壞。
由此可見,伊麗莎白·普雷特約翰的研究揭示了現(xiàn)代性美學(xué)演進(jìn)中深刻的辯證張力,解構(gòu)與重建并非對(duì)立的兩極,而是同一枚硬幣的雙面。現(xiàn)代藝術(shù)的革命性不在于其反叛姿態(tài),而在于它通過自我否定實(shí)現(xiàn)了美學(xué)范疇的拓?fù)渲貥?gòu),使“美”在廢墟中生長(zhǎng)出更繁復(fù)的根系。
藝術(shù)的倫理:當(dāng)代美學(xué)的彌散與重生
在論述當(dāng)代藝術(shù)時(shí),伊麗莎白·普雷特約翰展現(xiàn)出令人欽佩的理論包容性。她將杰夫·昆斯的媚俗美學(xué)與埃利亞松的生態(tài)藝術(shù)并置討論,揭示出兩者共享的美學(xué)策略:將傳統(tǒng)“非藝術(shù)”的感官體驗(yàn)合法化。昆斯通過夸張的俗艷質(zhì)感解構(gòu)高雅與低俗的二分,埃利亞松則通過氣象裝置重建人與自然的美學(xué)聯(lián)系。
書中對(duì)全球美學(xué)流動(dòng)的分析尤為精彩。日本“物哀”美學(xué)在村上隆作品中的轉(zhuǎn)化、伊斯蘭幾何學(xué)在當(dāng)代建筑中的復(fù)興,這些案例表明21世紀(jì)的美學(xué)正在形成一種“翻譯中的傳統(tǒng)”。美不再是被動(dòng)繼承的標(biāo)準(zhǔn),而成為不同文化語(yǔ)境間主動(dòng)對(duì)話的產(chǎn)物。這種全球化視角使本書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的美學(xué)敘事。
伊麗莎白·普雷特約翰引導(dǎo)我們思考的是一個(gè)比美學(xué)更根本的倫理問題:當(dāng)藝術(shù)徹底拋棄表面之美的追求,它是否也切斷了與人類普遍情感的聯(lián)系?本書的深刻之處在于,它既不懷舊地呼吁回歸傳統(tǒng)美學(xué),也不激進(jìn)地?fù)肀氐椎姆疵缹W(xué),而是指出第三條道路:美作為感知藝術(shù),要與接受者之間存在某種程度上的“共情空間”,從而使得藝術(shù)避免淪為封閉自戀的系統(tǒng)。
在人工智能生成藝術(shù)、虛擬現(xiàn)實(shí)體驗(yàn)日益普及的今天,《美的,藝術(shù)的》不僅梳理了過往的美學(xué)史,更啟示了未來。當(dāng)技術(shù)可能徹底改變藝術(shù)的生產(chǎn)方式時(shí),伊麗莎白·普雷特約翰提醒我們:美的本質(zhì)或許就在于它永遠(yuǎn)不能被完全定義,它始終作為藝術(shù)的隱秘維度而存在。正是這種辯證思考,使本書成為理解當(dāng)代藝術(shù)困境與美學(xué)復(fù)雜性的必讀之作。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