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董小玉 盧松巖
在物質高度豐沛的當下如何充盈個體的情感世界,這已成為一個社會難題,甚至堪稱世界性的困境。德國學者伊麗莎白·馮·塔登在著作《自我決定的孤獨:難以建立親密感的社會》中指出當下人們所普遍面對的情感困境,即人與人之間似乎越來越難以建立一段充滿親密感的關系,作者啟發我們要勇敢地走出自我設限的人生,在與他人的親密關系中享受自己的人生、追尋自我的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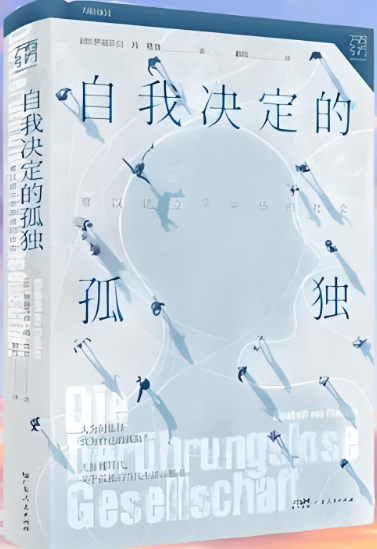
親密關系的悖論:渴望親密又恐懼傷害
2025年2月8日,民政部網站公布《2024年4季度民政統計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結婚登記610.6萬對,比2023減少157.6萬對,降幅為20.5%,這一數字創下1979年以來的最低紀錄。據此可以看出,當下社會中的親密關系建立情況十分嚴峻。然而,與這一數據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網絡戀人、游戲陪練、“搭子”社交等新興職業與社交模式的興起,這暗示著人們內心深處對親密聯結的渴望并未消減。針對這一矛盾,伊麗莎白在本書的開頭便直指當下人們所面臨的情感悖論: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矛盾的想法,既渴望親近,又希望得到保護,不被那些違背自己意愿的親近傷害。這為我們理解當下人們親密關系困境提供了新角度。
自我決定的孤獨:親密關系悖論的時代推手
何以形成這樣的情感悖論?伊麗莎白將其歸因于“自我決定的孤獨”,其背后是數字媒介與商業文化的推動。
一方面,數字媒介的快速迭代升級,使其具備了高度仿真性的溝通效果。人們在面對由一段算法程序模擬出來的數字形象時,往往被這種新奇的體驗所吸引,而這種算法程序總是按照使用者在數字媒介中的使用習慣而生成。相比真實的、具備主體性的人類而言,它們往往更能契合使用者的心理需要。但伊麗莎白指出:“對數字設備的依賴或許能夠減輕人類對孤獨或者死亡深深的恐懼感,但是這種依賴同時也會減少移情的能力,使人習慣于身體接觸的缺失、離群索居的強大影響力以及對虛擬生活的偏愛。這種依賴滋養著自戀,鞏固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方式和對自我的美化,最終導向一個封閉的‘自我’。”
另一方面,商業文化則對“自我”概念進行了工具性的塑造與強化。商業文化中著重強調“自我”的價值,并美其名曰“活出自我”。但事實上,商業語境中對自我的追尋往往是缺少主體性的,或者說它是對消費主義的追求,對一場又一場華麗的時尚符號的追求,這就掏空了“自我”的內涵,甚至異化了其本真的意義。商業文化還會通過不斷強調“自我”的瑕疵來刺激人們不斷通過消費來彌補瑕疵帶來的焦慮,繼而陷入自我貶值的困境中。伊麗莎白指出,自我的不斷貶值,是我們為了不斷提升自我價值而付出的。我們越來越難以平和地接納自身,無論付出多少努力,總因感知到“弱點”而陷入不安。在這兩方面的作用下,人們越來越執著于自身,為提升自己、緩解自身焦慮而殫精竭慮、耗盡心思,從而難以有充分的精力去與他人建立一段親密關系。
勇敢走出自我的牢籠:后物欲時代的自我救贖
伊麗莎白引用了福克斯“具身的自由”的思想來幫助我們應對這樣的情感困境。這種自由的目的并不是去征服軀體,而是要在真實的人際關系中、在愛欲互動中、在心智交流上培養軀體的感官和感覺能力。它意味著不要去重塑自身,而是在與他人的相遇和身體間的親密接觸中真實地活著。“具身的自由”著重強調了與他人建立關系的必要,同時調和了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系。它啟示我們,親密關系并非要求一方對另一方毫無保留地接納或自我的完全消融,而是可以在保有自身特質的基礎上,與他人建立深刻的連接。
伊麗莎白還認為,在親密關系中幸福與甜蜜并不是唯一的內涵,它還必然包含了辛酸與苦痛。但伊麗莎白還指出:“疼痛同樣也標志著具有決定性的差異性。能夠感受到疼痛的人就是活著的,也就能感知到一個有生命的自我。”事實上,我們在這種不可避免的痛苦中反而更能促進親密關系的發展。
將目光投向當下中國社會,我們正逐步邁入社會學者鄭也夫所定義的“后物欲時代”。鄭也夫認為,隨著物質財富的積累,人類社會生產的快速發展使得長期困擾人們的溫飽問題得到基本解決。從此,人類社會向饑餓記憶告別,進入了“后物欲”時代。在這一階段,隨著物質水平的提升,人們對情感的追求也水漲船高,親密關系的目的便從原本的“經濟共同體”逐漸轉向“情感共同體”,對親密關系中情感價值的看重成為人們建立親密關系的核心訴求。
從這一角度來看,我們當下社會中所面臨的情感悖論、情感失序等問題,一定程度上也是這種時代變遷帶給我們的情感變革,如何更好地在一個物質充裕的時代下,享受到高質量的情感關系將是這幾代人需要應對的問題。伊麗莎白在本書中給我們提供了極具價值的參照,她鼓勵我們勇敢地打破自我設計的牢籠,走出數字媒介和商業文化的陷阱,在真實的社交中去完整地感受親密關系的快樂與痛苦,去體驗那些我們未曾設想過的生命經歷。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